梦的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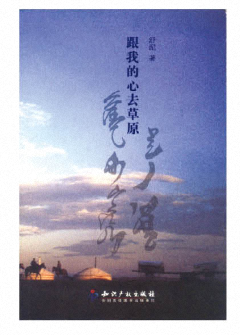
梦的去处
——《跟我的心去草原》之序
文/宝音贺希格
(一) 舒泥有个梦,是“三十年的悠悠长梦”。她说,这跟那位生长在台湾的东北人无缘无故地梦到一片草原,又无缘无故地喜欢契丹的历史一样。这“无缘无故”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形而上的“缘故”,那是与生俱来的,是神秘莫测的、难以言表的生命暗示。
一个蒙古人问舒泥:“你为什么会喜欢我们这个民族?”她回答:“我就是喜欢,不为什么。”这如同“没有任何预兆,莫尔根的妈妈唱起歌来,令人惊叹的明亮、动人”,自然而然,不需要任何注解。
喜欢自己的梦,除了梦本身,还需要什么理由呢!
无缘无故,不为什么,没有任何预兆——梦就是如此。所有的理由,都会妨碍它自由自在的飞翔。
舒泥的这个梦,应该说是源自一种莫名的怀念或者毫无所求的留恋。所以她说,“那些故事是我记忆中的,我上辈子的故事”。如果说,梦是圆的,那从上辈子到今世——这个距离只是它的半径而已,因为梦者的记忆一直在延伸。
对于前世的追溯,似乎决定了她今生行走的方向。在梦的牵引之下,她上路寻找自己的蒙古,用镜头用文字用脚步——用心去接近着她所信赖的梦。
山峦在“低低地、缓缓地隆起,又缓缓地、远远地沉降下去”,如同长调;英雄从草原深处走来,又向草原深处走去;不知是美丽还是危机,马兰花“蓝幽幽地一直开到天边”;“令人感动的真诚”与“扶马背不朝前送的冷漠”同时存在;“能把忧伤压抑到扁平,然后用音乐送到无边无际,最后落到人心上,共振一样的颤抖”的、无人可比的布仁特古斯;“可以让七尺男儿热泪盈眶,也可以让襁褓中的婴儿安然入睡”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清晨,带着一种坚守的高贵给父亲备鞍的”萨其日拉图……
我跟着一颗敏感的心去草原,去历史,又回到现在,走向未来。这是我在舒泥的文字里发现的去处,也是她对自己的蒙古的一次次确认。
这条确认的路,漫长,伴随着诸多新的发现。她说,自己踏上的那些土地并不像自己所梦到的——“太奇怪了,我从没有看到一块土地和我梦里的土地相同……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对,科尔沁有农田,巴彦布鲁克有水坝,克旗有比蒙古包还多的旅游点,乌珠穆沁有网围栏,呼伦贝尔有新耕的土地……”这样的发现,多少有些意外,也带着些许的悲伤。今世的草原与前世的梦,相去甚远。在此,她的笔锋指向所谓“发展”造成的伤痕。这个伤痕,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和生命意义上的。因此,她说,“留住游牧民族!留给今天一份美好,留给未来一个希望”。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她的梦。
“只有我在哈拉和林登上度假村后面那座山包时看见的那条河,是个例外,没有堤岸,没有河道,恣意奔流,仿佛在梦里见过”。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里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她的梦,跟那条河流一样,以自由为轮廓,毫无拘束,自然流淌。随之,“蒙古”也变得不是只属于一群人的标签,而是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甚至是一种庞大而纯粹的精神隐喻。
在梦的按语里,在寻找的路上,舒泥开始意识到“蒙古是生命的一部分”。这里有热血的流动,在发出与大地有关的声音。在追寻我是谁的这条道路上,她的这个意识多么难得。这也是她回头寻找“我的家”的开始。“我的家”是属于生命的,是超经验的。 (二) 她说:“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尝试理解他,接纳他的痛苦和欢乐,站在他的角度上想问题,为他的成功而兴奋,为他的荣誉而骄傲,也要呵护他的伤痛,容忍他的缺陷。”那人,不止是一个人,在舒泥这里是一个民族,是一片土地,是她蓝色的故乡。与一个民族恋爱,也许是舒泥最大的发现。
曾经,舒泥与“蒙古”,也有过一段“彻底”而“干净”的割断。她说:“干净到我自己都记不得自己丢什么了。”这是她大学毕业那年的事情。但是,多年以后,当回头找寻之时,她不禁说:“尽管很多年了,我依然能认出来,原来什么都没忘。”这是一次对先天记忆的确定。“真正重要的是北方的山巅上向远方延展的草原,是我心灵深处岩浆一样翻腾喷涌的热爱。”由爱而生出的乡愁,沉淀成她生命的底色——永远无法抹掉的“Blue
Mark”,所以,可以这样说:她的梦,悠悠30年,从未中断。
如果说,舒泥喜欢蒙古,是从小女孩的时候,甚至是从上一辈子开始的,并且是“不为什么”,那么“割断”之后的“返回”,是因为三宝——“我发现我原来是一只被人养大的狼,多年以来一直为做一条好狗徒劳地努力着,那一天我听到了一声来自天际的狼嗥。我忽然明白我这些年少了什么——蒙古。那一天起,我决定返回。这话说起来重了,三宝改变了我的人生,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她听到了天际的狼嗥,听到了音乐,当然,更重要的是听到了原本的自己。狼与好狗的区别,在于不羁和顺从。回归自然,回归生命的本真,缘于一个美丽的理由。这个理由,顺其自然,毫无勉强。她说:“蒙古人喜欢歌舞很大的原因是蒙古人不大相信那些说出来的东西。”这个理解是独特的。她在倾听蒙古“无言”的部分,那就是音乐。我相信,理解、接纳、呵护、容忍自己“恋人”的人,才能听到对方的无言部分。
“三宝的音乐,在不了解蒙古文化的人看来就像个谜。大气、凄凉、唯美、严谨、叛逆……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应归为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风格在他的音乐里浑然一体”。她知道,这些东西原本是统一的。甚至她自己的文字里也带有这种对立的统一,这来自于舒泥与众不同的内心感悟。
“……如果我说,蒙古男人有山一样的温柔,蒙古女人像水一样的坚韧。你可能觉得我在写诗,用自相矛盾的话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在蒙古高原上,山真的是温柔的,山的曲线像舞动起来的巨大丝绸,但又是凝固的,深沉而博大;水真的是坚韧的,倔强、坚强、坚韧不拔,在那样平坦的容易渗透的土地上,百转千回,艰难前进,用少得可怜的乳汁滋润辽阔的土地,从小草、鲜花到牛羊野狼,从蝴蝶、蚱蜢到游隼、苍鹰莫不是她的子孙……三宝的音乐中充满着这样的‘自相矛盾’,这让他在公众领域里显得与众不同,捉摸不定。”这段话的透彻力,让我震撼,尤其是“山一样的温柔”和“水一样的坚韧”,充分表明舒泥的梦,走得很远很高。这样的认识,来自于她与蒙古的相识、相恋、相知、相守的“四重奏”。 (三) 她这本书里,既有与我共有的“蒙古”,也有只属于她自己的“蒙古”,后者更让我感到欣慰。我不会去问她“这是为什么”,也不希望所谓的“蒙古人”们对她抱有什么“感激之心”或者某种“优越感”。那是她热恋的梦,别人无法惊动。
“绕过干草垛,一所房子从地平线的方向跑过来,这是一户牧民的冬营盘。”舒泥如是说。是的,“我的梦土”上的去处,都会自己跑过来,这绝不是错觉。
《跟我的心去草原》,我断断续续读了将近半年,这也是一种慢慢倾听的过程吧。
如果是在那片辽阔的心灵故乡,这种“拖延”会让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这与前世有关,与无尽有关,不用着急。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被处于“生态与文化的孤岛”上,“孤岛”,既是空间,也是时间,所以我还是深感内疚。
我觉得,再多的语言也无法诠释好引领我去草原的梦,只是在一些摘录中穿插着自己的只言片语,记录了我的一点心得,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