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区域文化特性 (敖•查赫轮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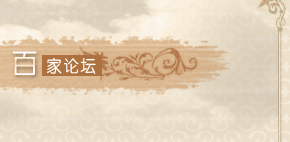
论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区域文化特性
敖•查赫轮(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民族学系博士)
摘 要: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化内涵深刻,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必须关注这些因素。在蒙古族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字尚未出现,各种知识体系尚未被严格界定时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总会担负承载和传播传统知识及生存理念的重任。因此蒙古民间文学是范围广泛,内容深刻,集文化、知识、艺术于一体的草原文明体系一环。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作为蒙古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反映的是区域族群对其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总体理解,是对整个草原文化的存续价值及人文特性的深层解读。关键词: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区域文化特性一、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文化区域特性 巴尔虎和布里亚特是居住于内蒙古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古老神奇的部落。他们曾在贝加尔湖东岸长期游牧,后来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迁徙到今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以西的巴尔虎草原、蒙古国东部地区、察哈尔、齐齐哈尔、青海、新疆以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在蒙古国东方省“达什巴勒巴尔县、巴彦栋县、巴彦乌拉县居住着布里亚特蒙古族,在古尔班扎嘎勒县和呼伦贝尔县一带居住着巴尔虎蒙古族和乌珠穆沁蒙古族。”(1) 从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南部的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忽真脱古木)一直到呼伦湖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地带是山地、河谷、草原交叉纵横的地方。其地形序列如下:世界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及色楞格河入湖区、贝加尔湖东岸平川谷地及低山丘陵、蒙古国肯特山和它的延续俄罗斯境内的雅布络诺夫山、博尔朔夫山、鄂嫩河及其河谷地区、克鲁伦河和蒙古国东方草原、苏杜尔图山、呼伦湖、贝尔湖、额尔古纳河、根河、海拉尔河、辉河、伊敏河、大兴安岭西麓。其中,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以东,大兴安岭西麓五陵以西的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水草丰美的大片高平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呼伦贝尔草原。肯特山海拔高度为2000m,贝加尔湖湖面海拔455m左右,呼伦湖湖面海拔540m左右,呼伦贝尔草平均海拔700m。贝加尔湖和大兴安岭之间的广袤高原丘陵地带的最高点为索杭图山,海拔为2507m。这片地势平坦的半干旱草原和低山丘陵地带的特点是广阔、天然、土地肥沃,气候条件相对好,适合于经营畜牧业生产,从而奠定了游牧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尤其是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麓的以巴尔虎各旗版图为主体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其水草丰美和富裕辽阔闻名于世界。《内蒙古自治区地理》里这样写道:“呼伦贝尔高原,地处于内蒙古高原的东北部,大兴安岭北段西麓。在第三纪初期已呈起伏不大的准平原形态,并于喜马拉雅运动时发生断裂与挠曲,东、西部隆起为低山和丘陵,中央陷落堆积成深厚第四纪砂砾沉积层的宽浅谷地平原,地面十分平坦,有‘砂质平原’之称。地势东南高,略向西北倾斜,海拔600—800米。地表水系发育,水资源比较丰富,天然草场优越,植被是以羊草和针茅为主的草甸草原与典型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牧场和重要的牧业基地。”(2)曾在《旧唐书》中出现的“蒙兀室韦”部落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的。“蒙古秘史”里首先提到的苍狼,花鹿西迁起点也在这里。因此,呼伦贝尔市巴尔虎草原所拥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优越性与传统社会文化适应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蒙古族独特的游牧文化集中区域。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祝颂词与故事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在这种的生态地理环境中萌芽、发展的。 在古老的“拔野古”时期,狩猎和游牧经济是巴尔虎诸部落的支柱产业。他们长期在美丽辽阔的贝加尔湖(汉代称它为“北海”、突厥人叫“富裕之湖”)一带生存和活动。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他们以经济和社会资源。公元647年拔野古被唐太宗置为“幽陵都督府”,其地在今呼伦贝尔市境内。这在表明巴尔虎部落早已开始了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历史文化渊源。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的次年,巴尔虎等“林木中百姓”归附蒙古。1577年俺答汗子在青海建寺毕(仰华寺)时巴尔虎彻辰岱青等随俺答汗前往青海。巴尔虎部落颠沛流离,东迁西徙,一直到十八世纪初期正式入住现在的呼伦贝尔草原,并成为主人公。“1732年,居住在布特哈的巴尔虎壮丁275名,被编入‘索伦八旗’,驻防呼伦贝尔。1734年,居住在外蒙古车臣汗部的巴尔虎兵丁2894人,迁往呼伦贝尔,被编为‘新巴尔虎八旗’。”(3) “巴尔虎”这个词在史料和口传中读法和写法众多,后人对它的解释也五花八门。现在多数学者对该词的解释正趋于接近,即“巴尔虎”一词初现于公元4世纪。最初来自于代表英勇无比的原古神犬之名。此名后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之名,并逐渐成为整个部落称呼。 呼伦贝尔市布里亚特人的迁徙与居住历史相似于巴尔虎人。布里亚特蒙古族最早也居住于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并以畜牧业为主,以渔业为辅,信萨满教,过着相对安稳日子。16世纪末,他们与蒙古族其他部落一同接受藏传佛教,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由于众多原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部分人南迁到现在的齐齐哈尔一带居住;另一部分人到喀尔喀蒙古,并附属于达赉贝萨张其布道尔吉旗;剩下的部分人则北迁到故土尼尔秋河以及巴儿忽真脱古木一带。1918年,迁徙到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1922年附属于呼伦贝尔,并在锡尼河一带建立了布里亚特旗。这样,布里亚特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巴尔虎文化和厄鲁特文化交织在一起,经过漫长的相互同化过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域文化。 正如上所说,从呼伦贝尔西部的巴尔虎草原经由蒙古东方草原,到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儿忽真脱古木(指“巴儿忽真河注入贝加尔湖的下游河谷冲积平原。这里林木茂盛,可猎可牧,是一个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的好地方”(4)),几乎都是高平原、低山、丘陵、平川地带。整个地带具有地理和气候方面的相同特点。同时,自古以来巴尔虎部落和布里亚特部落社会历史来往较密切,经济生产和社会文化的同质性较高。因此现在的贝加尔湖一带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和中国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各旗在传统游牧生产和文化生活领域基本保持了相同特征。但需说明,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体系里以巴尔虎蒙古族和布里亚特蒙古族聚集区为中心的呼伦贝尔草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故本研究暂时不予重点讨论俄罗斯境内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文化现状。 生态和地理环境是人类文化被创造的基本自然条件。“天时”和“地利”之上才会有“人和”。“社会始终在无意识地进行调整,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5)在气候、温度、降水量、地形、土壤、自然灾害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化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和群体性。居住在寒带、温带、热带地区的各族群文化类型及特征各不相同。同样,居住在高山地带、平原地带和海洋岛屿的人们所拥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存理念和行动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生态环境和自然地理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生态多样性,并促进了多元文化及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势。 在平坦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游牧几百年的巴尔虎蒙古族创造出与其自然生态环境相符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文化--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 (一)从历史角度分析,巴尔虎部落历史悠久,迁徙万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复杂多变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己独特游牧文化。从巴尔虎•布里亚特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原始社会狩猎采集阶段典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遗迹及稍后的游牧社会文化发展特征。在保持和发展蒙古族传统游牧社会基本结构及文化特色方面,巴尔虎•布里亚特人具备了独特的口头传承方式和丰富的人文素质。而这些在实际操作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承接与社会稳定作用。在目前的中国,呼伦贝尔市巴尔虎•布里亚特人所拥有的游牧文化和民间文学遗产很具特色,颇为典型。 (二)从政治地理学角度分析,巴尔虎草原距中原地区2000公里,以大兴安岭相隔于东北农业区域,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赤塔州等相望,因此在古代和近现代征战与冲突中总是相对独立生存于天然防线较突出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游牧经济文化的季节性、流动性、适应性很强,不太容易受到持续而严重的人为威胁,故有利于保证其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换句话说,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初期,巴尔虎部落在地理和文化方面所受到的外部袭扰和影响较小。就这样,在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布里亚特人创造出特色较浓的区域游牧文化。 (三)从区域经济与环境角度分析,“呼伦贝尔草原牧场辽阔,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盛,河湖遍布,是世界上生态保持较好,未受污染的大草原之一。”(6)但由于巴尔虎草原地处于北纬温带和亚寒带交接处的大陆型气候,种地条件较差,收获成本较高,每平方公里能养活的人口密度低,故历史上越过大兴安岭定居于这里的各地农民较少,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巴尔虎游牧经济文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经过两多千年的文化积淀和积累,巴尔虎文化已发展成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有历史悠久的文化既然定型就不太容易自愿接受外地文化并被其同化。虽说游牧文化是较开放的,但也不能低估其内在稳定性和排他性。 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创造出独特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同样,独特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保住了独特的呼伦贝尔生态环境。生态和文化是相互分不开的,而且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所以它也同样受到生态地理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将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文化放在这种生态地理总体环境框架里加以研究,才能悟出其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地域特性。二、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 “作为蒙古族文学之源的神话传说,自产生之日起,对自然界和史前社会生活的折光反射,几乎是五光十色,包罗万象。这一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多方面功能,反映了蒙古先民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原始思维成果,无疑对后世蒙古人的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的构成和发展,对他们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起了启蒙和奠基作用。”(7) 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发源地贝加尔湖附近曾产生众多神话传说,且与大自然尤其湖泊崇拜心理紧密相联。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索博尔霍湖们于叶拉夫宁斯基区贝加尔湖湖系与勒拿河分水岭熄灭火山边缘的断层地带。它的直径只有30米,深度竟然超过20米。这个湖泊经常发生人畜神秘失踪事件。“关于这个神秘的湖,当地流传着许多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年成吉思汗打下天下后,作为天子,按传统要上天去接受权利的传承,他的士兵们也要上天接受检阅。阅兵时,成吉思汗看见一个士兵久久地盯着自己,这当然是大不敬了,一怒之下成吉思汗将身边的长矛掷向那个士兵。士兵一缩头躲过了致命一击,但长矛的力量如此巨大,顷刻间山梁崩塌、大地坍陷,成盆地。这还不算完。长矛直往下落,直到钻出水来……所以一直以来当地居民认为:这个湖没有底。而历史上的古布里亚特语中,索博尔霍正是‘无底’或‘穿透’的意思。”(8) 贝加尔湖的最大岛屿奥里宏“岛上的布尔罕神也叫萨满悬崖,是萨满教亚洲九大圣地之一。在布里亚特人的神话中,悬崖的洞穴里住着布尔罕神—贝加尔湖的统治者。附近湖边还有缠满布条的树,是用来祭拜布尔罕神的。”(9)古老的巴尔虎和布里亚特传统生命的根基毫无疑问是纯朴而神秘的大自然。 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古老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文化区域流传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并其深层文化涵义至今犹存。这些神话传说大部分都创造于原始部落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得到改动、润色、充实,但基本模式和内容特色却没被改变。神话是蒙古族古代先民以自己特有的幻想形式和理解方式对自然万物来源和各种现象作出的各类解释。神话所携带的真实因素相对少,夸张和想象出来的东西相对更多。传说则是自然环境、历史事实和生活真实之艺术化反映,它既具有真实因素,又不缺提炼和夸张的成份。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所承载的原始文化和自然生态崇拜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正如在拉施特《史记》中所记载的传说《额尔古涅—昆》所反映的那样,大多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主要根据社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纪念以及山川河湖的景色,通过原始思维和艺术幻想加以润色、加工、夸张、修饰而产生的。许多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所折射出来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真实、原始思维和宗教信仰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于了解和研究原始生态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地域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关系来说极为重要。另外,巴尔虎神话传说是蒙古族现存的原始神话传说当中,不管数量上,还是完整程度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后来创作的《舌战陶王》、《明断盗牛冤案》等诸多传说虽说原始文化内涵有所降低,但其历史和教育价值仍然颇高。三、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 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相同生态特质、历史渊源和悠久的文化传承特性决定了他们在民间文学文化含量及特色上的共同性。英雄史诗在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宝库里占有重要位置。 (一)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研究概况 目前,在蒙古族聚居区所发现的史诗已超过300部,是世界上英雄史诗最多而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巴尔虎、扎鲁特和新疆卫拉特地区是我国蒙古英雄史诗三个中心。再加上伏尔加河—顿河一带的卡尔梅克蒙古、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蒙古和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以及喀拉喀地区,可以说,世界上现共有7个蒙古英雄史诗中心地区,而其一即巴尔虎草原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甘珠尔扎布、仁钦道尔吉、道荣尕、陶格陶胡等人在巴尔虎地区前后记录了10多部史诗的40多种异文,其中有《阿拉坦嘎鲁》、《珠盖米吉德夫》、《巴彦宝力德老人》、《阿布拉尔图汗》、《希林嘎拉珠巴托尔》、《陶干希尔门汗》和《阿拉坦曾布莫尔根夫》、《三岁的古纳罕乌兰巴托尔》和《喜热图莫尔根汗》等史诗。”(10)在史诗搜集人员当中“最早发现和出版巴尔虎史诗的是甘珠尔扎布先生。1956年出版的《三岁的古纳罕乌兰巴托尔》里选入的三部史诗是由他搜集,并由现代著名诗人那•赛音朝克图审阅。”(11)其他巴尔虎史诗被选入于《希林嘎拉珠巴托尔》(1979年)、《蒙古族民间故事》(1979年)、《那仁汗史诗》(1981年)以及《勇士布拉岱汗与卷鬃马》(1995年)等选集。呼伦贝尔巴尔虎人称史诗为“故事”、而布里亚特人则称其为《历史》,(蒙古语叫“途和”)。巴尔虎的故事说唱者和布里亚特的历史讲说者们在史诗讲述方面具备极为相似的特点。这也是我们在相关研究当中将巴尔虎和布里亚特放在一起加以分析的原因之一。在蒙古文学近几百年发展史上“故事•历史”总是代表着虚构程度较高的文学体裁概念。1928年,蒙古族现代文人特睦格图在他《新评译〈三国演义〉跋文》中首次提到了文学的虚构性和历史的真实性问题。(12)但从民间文学有关类型术语可以看出,不管“历史”,还是“故事”都不能离开其文化根基与生活土壤。其实,蒙古族英雄史诗本身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真实历史”。在这部庞大的艺术化历史里储存着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巴尔虎•布里亚特史诗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 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研究已初具规模,几代研究人员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这在蒙古语区域文学研究或区域文化综合研究领域尚属少见。 (二)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主题 婚姻和征战是蒙古族英雄史诗里普遍出现的两大主题,巴尔虎史诗也不例外。婚姻主题“反复讲唱一个英雄到遥远的异地他乡求婚娶亲的过程,或恶魔蟒古斯入侵英雄的国土,掠走霸占英雄的妻子而引发战争。这里明显反映了从蒙古民族开始形成的族外婚制度。”(13)蒙古族英雄史诗婚姻主题总是与征战主题及收复失地等初级社会政治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婚姻是人类社会基本组织—家庭形成和存续的保证。“家庭决定于婚姻,而家庭又是社会的全部稳定性的基础。”(14)原始氏族社会末期,随着原始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基本结构和经济生产关系重新组合和整合,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开始取代原始婚姻模式。尤其在部落社会到酋邦(Chiefdoms)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战争很可能成为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因此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以婚姻—征战为基本主题的同时,这两个主题总是结合在一起,以反映氏族与部落社会晚期发展阶段的复杂程度和多变状况。 (三)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价值 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形成于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大领域的形象反映。蒙古族古代社会许多事态目前无法再现或考证,因为眼前有关研究已证实蒙古文的记载历史可能不超过1000年。根据蒙古族口头传承的文化传统,通过对巴尔虎英雄史诗等原始先民“口承史料”的细致研究,可以发现和了解史前史基本社会形态和整体存续状况。 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是在辽阔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牧民的原始思维、传统知识、行为方式及生存哲学的艺术化表现。它既是蒙古族民间文学杰出作品,又是“百科全书”式历史资料。四、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与祝颂词 (一)民歌 辽阔富饶的绿色草原创造了民歌诞生的天然条件;勤劳勇敢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牧民创造出了数以万计的民歌。如果说鄂尔多斯是“歌舞之海”,那么,呼伦贝尔也可称作“民歌之洋”。 经过千百年的词曲提炼和艺术扬弃,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具备了如下特点: 首先,辽阔平坦的草甸草原和半干旱草原是民歌之洋形成的自然基础;换句话说,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里跟草原无边宽广和雄伟壮丽的形象高度一致的民间长调(乌日汀道)特别丰富。《辽阔的草原》、《褐色的鹰》、《富裕巴尔虎的更夫》、《轻快褐色的马》、《溜圆的小白马》、《富饶明亮》等一大批歌曲属于此类。这些歌曲音域宽阔,音调悠长而高亢,曲调素朴而自然,旋律美妙,风格宏伟,歌词通俗且充满哲理味道。“到了约公元七世纪,诸蒙古部落开始由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迁,纷纷跨入蒙古高原,并从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逐渐过渡到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为辅的经济形态。从这个时期起,便产生了乌日汀道(长调)。由此可见,乌日汀道的生产和发展是和浩瀚无垠的大漠草原及游牧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而且,从目前的乌日汀道的主要分布情况来看也大都在广阔的草原地带,即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北部、巴彦淖尔盟北部及阿拉善盟等地。”(15) 其次,千百年缓慢形成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社会文化是民歌之洋永远汹涌澎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和社会过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群体关系、交际方式、问题处理机制等都自然成为一大批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另外,对对外来往、族群关系、征战与共处的认识也决定了一部分民歌的内容。例如,《宝格达山森特尔》、《父母俩》、《阿日库布琪》、《席勒原野之草》、《落叶松》、《兴安河麻雀》(一、二,布里亚特民歌)、“荐骨之歌”(一、二、三、四,布里亚特民歌)、“幻景中的原野”(布里亚特民歌)等都是较典型的这类歌曲。这类歌曲的文化内涵非常深刻,影响深远。相对而言,巴尔虎民歌里抒情歌曲或抒发感情的成份较多,布里亚特民歌则叙事部分较突出。《兴安河麻雀》这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歌谣创造于“16世纪末俺答汗时期。《布里亚特蒙古简史》里这样写到:现在的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牧民中有这样的传说流传着。这是(16世纪末)蒙古俺答汗的女儿巴拉金嫁给布里亚特布贝贝勒当其夫人,并跟车队翻越大兴安岭时唱出来的歌曲。”(16)因此,这些歌曲主要折射出巴尔虎•布里亚特人对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心态。 再次,对大自然的感情,亲戚朋友的亲情与眷恋,爱情的尊崇以及对牲畜的宠爱也创造出了大批情感歌曲。其中,热恋故乡的,想念父母的,赞颂五畜的,情深意远的爱情歌曲较为突出。《把心爱的小妹留在了巴尔虎故乡》、《孤独的白驼羔》、《膘肥的白马》、《额尔敦乌拉山远影》等歌曲都属于此类。 第四,巴尔虎•布里亚特是蒙古族古老民俗风情较完好保留着的地区。同时巴尔虎•布里亚特东北区域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环境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故自然形成了特色较浓的民俗风格。与这些民俗风格紧密相联的民间歌谣非常丰富。婚礼歌曲、那达慕大会歌曲、祭祀歌曲等属于此类。但部分歌曲已趋于整合,以表达多层内涵。比如,“将八个哈那的蒙古包……”一首歌曾这样唱道:“将八个哈那的蒙古包/扔弃在搭建中。/将八十岁的母亲/遗弃在病床上。/将八座白帐篷/扔弃在搭建中。/将八十只骆驼/丢弃在秋风中。/将两千只羊丢弃在棚圈中。/将二十五岁的妻子/为什么要执意抛弃呢?”(17)这首歌其实集情感、哲理、民俗于一体的综合性歌曲。 第五,巴尔虎•布里亚特现代歌曲在传统文化及民间歌谣上形成而传遍的。因此巴尔虎现代歌曲除了一些现代因素以外,在曲调、音域、内涵和情感方面与传统保持了高度一致。 第六,歌手和歌迷较普遍是巴尔虎•布里亚特歌坛的特点之一。在蒙古族歌坛上享有盛誉的顶级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是巴尔虎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布里亚特的郝木板道尔吉也是闻名远近的老歌唱家。 第七,巴尔虎民歌节奏轻快,音域宽阔,曲调悠扬;布里亚特民歌则节奏丰富,风格轻快、明朗。歌舞并行,雀跃欢呼是布里亚特传统歌曲重要特征。(二)祝颂词 蒙古民间文学海洋里祝颂词占相当比例。祝颂词是由祝词和颂词组成的。“祝词是通过反映人民生活、劳动等各种社会现象来祝愿对方未来美好生活的,在民俗活动和公共仪式上念颂的,与民俗有紧密联系的专门诗歌。”(18)颂词则是“在叙述和形容指定对象时,所表达出来的以赞颂意义为主的传统诗歌。”(19)祝颂词总是与古老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较长篇幅的诗歌形式出现并被传诵到各地民众,故其在民间文学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呼伦贝尔草原地形地貌、自然风光、环境气候与其他蒙古族聚居区有所不同,因此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与其他区域的蒙古族祝颂词基本保持一致的同时,还具备了某些自己特色。 首先,广阔草原四季变化和传统文化叙述方式深刻影响了祝颂词基本叙事模式和主体内容。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在叙事、抒情及结构安排上独具一格。 其次,原始民俗文化和自然崇拜因素较完整地承载于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 蒙古族祝颂词可分为如下三类: A、15世纪前基于萨满教、自然崇尚及祭祀与信仰仪式而形成的,祭祀色彩较浓,词行数相对少的初级或原始祝颂词; B、16—19世纪在接纳和吸收藏传佛教文化的同时,内容和内涵上被适度改造了的多行多首变异祝颂词; C、从20世纪开始重新被搜集整理并结合于社会环境及时代特色的,文人主动创造的,脱离严格的传统仪式而独立存在的新型祝颂词。 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这与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原始自然风貌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有密切联系。由于历史原因,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和陈巴尔虎之间“在信仰、服饰、婚姻、礼仪、发音等方面形成各自的不同特色。”(20)布里亚特苏木与巴尔虎旗之间的这种地域差异相对而言更大一些。这点在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里可以看到。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区域整体,共同因素远多于差异性。 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的文学与文化特点如下: 第一,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巴尔虎风俗习惯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 第二、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该区域人们关于长远利益和循环哲理之完美化了的认识; 第三、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所突显的是人,所以它能验证蒙古族传统理想主义思想和人本现实主义思想结合点之合理性; 第四、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巴尔虎传统文化的载体、传播者和知识积累者。 第五、巴尔虎•布里亚特祝颂词是蒙古族传统诗歌中数量众多的,表达方式灵活的,诗歌语言得到空前发挥的民间文学遗产。《蒙古包祝颂词》和《婚礼祝词》可以证明这点。五、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区域文化涵义 文学是文化的内化载体,民间文学是民俗和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和传播者。民间文学研究对于传统文化整体研究来说极为重要。 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区域文化是蒙古族历史上较早形成并较完整地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该区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总是携带和蕴含着丰富多彩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内涵。尤其在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祝颂词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类型当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精华。 (一)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不仅是巴尔虎部落古老生存活动的历史写照,同时又是蒙古民俗的真实口述。目前,不少人从文学和美学角度研究史诗的审美特色和形式特点,但实际上,史诗所反应和涵盖的不仅是纯文学或美学方面的东西,而且更为广泛,更大范围,更为全面的民俗与历史内容。除文学外,还需与历史、民俗、哲学、环境、心理、医学、语言、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相结合并加以研究。这对全面科学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巴尔虎•布里亚特地区不只是世界蒙古英雄史诗发源地或集中地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蒙古文字创造以前的历史或史前史。 (二)民歌和祝颂词也是古老草原人民的生活写照和行为缩影。如果民歌涉及到的主要是感情、思恋的话,祝颂词所体现出来的则是民俗、思维、心理、生态观念。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大部分为优秀的民俗歌谣,是该区域劳动牧民艺术才华表现之一。 (三)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文化内涵极为深刻,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必须关注着些因素。在蒙古族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字尚未出现,各种知识体系未被严格界定时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总在担负着承载和传播传统知识的重任。因此民间文学是范围广泛,内容深刻,集文化、知识、艺术于一体的传统文明体系一环。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作为蒙古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反映和体现的不仅是对该区域生态自然与社会文化的总体理解,同时又是对整个蒙古族古老文化存续价值及其人文特性之肯定。 (四)研究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时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利用综合知识,全面考虑和分析问题,并探索出传统文化内涵。更要强调研究使传统文化孕育成长的生态环境与自然地理。呼伦贝尔草原是巴尔虎•布里亚特区域文化形成和传承的根基。它是草原文化之母亲,蕴含着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生存哲理与人文艺术。因此对巴尔虎•布里亚特部的自然生态—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研究是至关重要。注释:(1)宝音主编:《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大学蒙古研究所、1991年、P37。(2)石蕴琮等编著:《内蒙古自治区地理》、内蒙古民出版社、1989年P21-22。(3)(4)(10)(孛•蒙赫达赉著:《巴尔虎蒙古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P494、P9、P426。(5)董建辉著:《政治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P127。(6)呼伦贝尔盟地方志办公室编:《呼伦贝尔盟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P43。(7)(13)荣苏和、赵永铣、贺希格陶克涛主编:《蒙古族文学史》(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P67、P234。(8)苏钰:《贝加尔湖心脏常刮风暴》、《环球时报》(异国风情)、总971、2005年5月30日、P21。(9)苏钰:《恐怖湖直径只有30米》、《环球时报》(异国风情)、2005年5月16日、P21。(11)陶格涛胡、拉斯格玛搜集整理:《勇士布拉岱汗与卷鬃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P2。(12)巴•格日勒图《蒙古文论集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P626。(14)EdwardB•Tylor著、连树声译:《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460。(15)好必斯:《乌日汀道在演唱中的时空感及其他》、《文艺研究论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P56。(16)巴图德力格尔、努玛搜集、整理、编辑:《蒙古民歌丛书—呼盟集(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P109。(17)宝音德力格尔、阿日布登搜集、整理、编辑:《蒙古民歌丛书—呼伦贝尔盟集(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P737-738。(18)(19)ш•嘎丹巴、X•散皮勒敦德布、Д•策仁苏德那木编:《蒙古民间文学》、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P169、P206。(20)朝•都古尔扎布编著:《巴尔虎风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P24。
百家论坛
草原文化研究、推动草原文化发展
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