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原文化的起源 (额斯尔门德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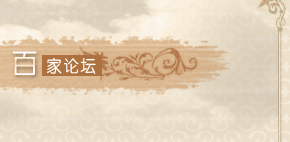
论草原文化起源额斯尔门德(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副教授)
摘 要:草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遍布于世界各地。我们所研究的草原文化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共同创造的文化。草原文化也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取决于草原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和游牧经济方式。本论文主要借鉴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界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深入探讨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探讨所谓人类文化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草原文化从何而来,其形成过程又如何等问题。关键词:草原文化起源游牧一、何谓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这一概念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我想首先探讨“草原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确定草原文化在人类文化形态系统中的定位和在理论领域里如何概念化的问题。众所周知,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本身的历史等同。但对于自己创造的“文化”的研究,就像人类对自己本身的研究那样,远远落后于人类对其他自然现象的研究。虽然古希腊罗马古典哲学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的人文主义思想里体现过与“文化”有关的思考。但是把“文化”真正当作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文化学的产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是美国新进化学派代表人物莱斯利•怀特开创的。到60、70年代旧苏联也兴起过研究文化的风潮。中国的文化研究之风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 尽管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历史如此浅薄,但其涉及的问题众多,学科之间的交错繁杂。许多学科都把文化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不仅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而且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神学以及文学、艺术学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文化的概念。就因为如此对文化的解释也就繁多。究竟何谓文化,至今尚未统一的答案。自从1871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的概念以来,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当然这也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关。据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C.克拉克的分析,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160多种,甚至更多。但是从中可以概括出人类对于自己文化的一些共识,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劳动创造的多种不同形态的特质综合体。人类一切文化都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并且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技术与工具的结合体。文化学界又根据文化的特征、内涵,把它详细地分类成为不同的类型。划定不同的文化圈。如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等。可是我们探讨的所谓“草原文化”这一概念是在文化学研究史中尚未有过的新概念。那么什么叫“草原文化”。在人类文化大体系当中如何确立草原文化的定位。孟驰北先生在他的近期著作中曾经探讨过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问题。阐述了草原文化的特征、性质和内涵。认为草原文化是以原始初民的冒险、进取、创新等活性精神元素为主导作用,以游牧民为传播信息载体的群体文化。中国草原文化专题研究的学者们却认为中国草原文化是中国北方历代各部族或民族适应蒙古高原生态环境、气候条件过程中创造的一种以游牧生产为基础的生态型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稳定的历史传承和久远的形成发展过程,具有多元性创造主体和复合性构筑形式。具有广阔性区域分布。它的基本精神是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诚信朴实。当然草原文化是人类文化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应具备人类文化的一般特征,也应有它的独特性。或者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的观点说明的话每个文化应有它的民族属性。也就是说没有民族属性和通过它表达出来的独特的特征或个性的总和的话,何许谈文化。草原文化的载体就是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是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特质综合体。“草原文化是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游牧诸部落、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形态。根据史料证实,在人类发展史上从史前时期到原始社会以及其后的较长的时期游牧民族在世界的很多区域里留下了活动的痕迹。但由于历史的原故有很多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混合,同化成为农业民族。譬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最早创立文明的苏美尔以及阿卡德、加喜特、亚述、赫梯、斯基太、萨尔马提、犹太民族等。真正成为草原文化创造主体的是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诸游牧民族。如,戎、狄、林胡、楼烦、匈奴、东胡、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室韦、蒙古等。他们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为舞台,创造和传承具有草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特质综合体—草原文化。为此可以认为草原文化是诸游牧民族的共同创造的。草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蒙古族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成为主要传承者。从而言之,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认为草原文化是诸游牧民族在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草原地带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创造的,以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生态型文化,草原文化是多元因素构筑而成的具有复合性结构的文化,它的基本性质是“动”而不“静”。是一个动态性文化。二、草原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 人类创造的任何一种文化特质不无其产生的地理空间,因为人类是以群体为单位,生活在特定的地理区间之中。从而人类的文化创造,必然受制于外部的具体环境地段。显然,文化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或者“对话”过程中。早在人类祖先出现于地球这个生存空间就遇到了为了生存而适应其周围环境的考验。从顺应环境到改造环境的认识进化过程中人类学会了从自然环境中得到生存所需物质的知识和技术。利用这种知识和技术不断和自然界交往,把它提炼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因而这种知识和技术系统的结构往往与其环境因素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环境,它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技术的选择。不同的地理环境给予人们选择不同的生存技术的机会。而利用这种生存技术不断去改变环境、克服不利于自己的因素,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性劳动。马克思理论认为劳动创造人类、创造文化。 人类为了生存而不断接触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了解和改造自然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富有不同地理特征的文化特质。今天人类技术文化虽然发展到宇宙空间,但它仍然以地理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为基础的。这就说明人类文化尽管发展到某种顶点,也永远离不开最适合于它的特定的地理环境。这就是“人是一种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1)所决定的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就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有机会把文化依照它的结构上的特质信息来类型化、区分化。也可以以它的发源中心区域为依据称之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欧美文化”、“亚洲文化”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在研究文化区域问题时发现“文化类型有它的地理条件…一种特质综合体并不是胡乱散布在大陆上的”(2)文化区域应呈同心、圆形分布,而地理障碍、动植物分布等因素对文化区域的形成产生扭曲作用的规律性问题。显然文化特质的形成和扩散与其地理环境不可分割的关系。就其客观的含义而言,地理环境仍是文化形成的决定因素。由此而言,解释文化特质与地理状况之间的关系是解决文化特质形成原故的关键。 在世界文化史上,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问题的探讨并非少有。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曾经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阐述过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在《论空气、水和地理》中从医学的角度阐述一个城市居民的健康和习俗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一个地区性文化的形成取决于气候环境的所谓“气候决定论”。他指出住居在寒冷地带的民族虽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缺乏智慧和技术,因此他们虽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但没有政治组织能力,不能统治其他民族。亚洲民族虽然聪明,但缺乏勇敢的精神,因此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而居住在他们之间的希腊民族,性格具有两者的共同优点,既有勇敢的精神,也有智慧。16世纪时,法国的布丹(1530-1596)在《理解历史的方法》中,首次明确提出,地理环境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开了“地理决定论”的先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人们受多种事物如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的支配,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他认为在影响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的诸要素中,气候的权力比一切权力都强大,由于各地气候不同,造成各民族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的不同,而这些差异又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还认为地理形势决定了国家的规模,而国家的规模则与其社会组织形式相关。国土峡小宜于共和制,领土适中宜于君主制,领土广袤宜于专制制。孟德斯鸠说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人们就不关心他们的自由,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而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所以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政体;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地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二者混合的政体。 黑格尔把地理环境视为世界历史舞台。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也是不同。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将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主要分为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地和平原,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以及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等。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生性好客和掠夺。第二种地理条件下居民主要经营农业,“于是土地所有权和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第三种地理条件却给人类无限的空间,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马克思对地理条件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有许多论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这种存在既有生理基础,又有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形式和职能。中国古代学者也曾经深明地理与文化的关系。 但是把文化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文化学却很少涉及文化特质与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在其构造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对某种文化特质进行结构分析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地理因素成分。譬如有关“马”的文化特质,通常说的“马文化”的结构中就会发现,其所以构成为一种文化或者实现一种文化现象来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构成为日常生活内容结构的一个部分,是因为“环境”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外部因素,对于它的形成赋予充足的可能性条件。“赛马”是马文化特质综合体中的一个竞技文化特质。游牧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赛马文化特质的形成是由人们劳作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首先赛马文化特质是由时间和空间的互动关系中构造出来的。在它的构造过程中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起者重要作用。可是通常人们把赛马文化特质看作“人”与“马”的组合体来理解,往往忽略地理空间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至少缺乏赛马文化特质是“人”、“马”、“地理空间”与“时间过程”的组合体的理解或解释。 威斯勒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化区域”的概念就是以造成文化差异的外部因素,也就是环境因素为先决条件展示出来的。他从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综合体的共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中找到,造成文化差异的一般原因“自然环境”与“种族环境”因素。并就整个世界的环境提出了与人类聚集区及文化相联系的三大地理范围,即丛林、台地、苔原。从他展示的地图看来,丛林地带包括热带非洲、南亚、东南亚大部、奥洲、加勒比、亚马逊;台地地带包括南欧、地中海南岸、小亚细亚、中国、西伯利亚南部,直至白令海峡,然后纵贯南北美洲的中西部。它从北至南越过巴拿马地峡,沿安第斯山直抵南方巴塔哥尼亚大草原;苔原地带包括欧亚的北部、加拿大、美国北部、巴塔哥尼亚的南部。文化类型就此分成丛林文化、台地文化、苔原文化。虽然这种文化的划分只是最大范畴的分类,而且侧重于地理学。但其中显示了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威斯勒的文化地理分布学说,在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成的关系时具有借鉴价值。他提出的三种类型中的台地文化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文化的大的范畴。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条件的角度进一步细化台地文化范畴,就会得到更为确切的文化特质综合体的共性—草原文化特质。也就是说在地理学的地理分布概念里找到鄂尔多斯高原以北,西伯里亚以南,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台地草原的地形地貌、气候、植被、河流等外在于人类经验组成部分的因素却对于这里的人类社会行为有着重要作用的依据。当然自然地理环境是否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特质问题须待进一步实证。可是,环境对人类适应于它的过程(文化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是显然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台地草原地理环境究竟如何,它对于曾经在这里生存的古代人类的行为有何影响。我们可以借鉴地理学的经验知识,进一步了解。 草原地理环境是一个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生态学认为自然环境是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变量的原因是因为如果“离开了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形、土壤、水分、植被、动物群以及矿产、能源等自然条件,离开了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切文化创造活动都会失掉客观的基础”。草原文化的基础是围绕着家畜、狩猎构筑的特质综合体。草原文化和人类创造的其他类型的文化模式一样,是人的社会性活动的产物。而人类社会性活动的性质往往无意识地接受其环境的偶然性决定。草原文化萌芽在台地地带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巧合,而是这一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定了人类在这里生存而需要的具有适合于这里地理环境的社会性活动。即狩猎或驯养生产活动。因此草原文化产生的渊源在于草原,草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草原文化的可能性。在更多的意义上讲草原文化特质综合体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其自然环境。就象生物有机体的生存和发育取决于其扎根的土壤、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一样,文化有机体之所以成为一个特质,就因为其萌芽的地理环境之不一。 从性质上看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而生态结构里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草原地理环境与草原文化的产生在其深层意义结构上有什么因果关系。或者草原文化本身在它的结构上如何内化于草原地理环境的客观因素。我们可以具体的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台地置于地球上的地理位置大致在北纬20度至30度。北至西伯里亚,东到大兴安岭,南抵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西至阿尔泰山。地质学研究表明横跨欧亚大陆的这部分台地是在地质活动中从海底凸起而成,因而其地形地貌起伏高度相差并不大,大致海拔高度为1000—3000米之间。地理表形结构主要山地、丘陵、剥蚀高原为基本类型。其中山脉大约占总面积的30%左右,主要有蒙古境内的阿尔泰山系、杭爱-肯特山脉及内蒙古境内的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这些山脉地形中占据优势的,是具有发育良好的土壤和植被覆盖的平坦的地形。富饶的山脉地形对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地,同时对狩猎野生动物为满足生物需要的古代游牧人群也提供了生存场所。 据《蒙古秘史》记载13世纪的蒙古部落在其生活方式上就有了靠山地地理环境的“山地牧民”和以台地草原地理环境为其生存空间的“草原牧民”之分。这就说明古代游牧人群就适应和利用其处于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并提炼出最适合于它的生活方式。学术界认为畜牧业是从野生动物的驯养开始的,其具体时间虽然尚未确定。但是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古代人类从狩猎过程中和野生动物不断接触,了解它们的性格并捕捉之后才有可能的。而山地地形对这种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和捕捉野生动物很可能提供有利条件。山地这个地理环境因素对草原文化特质综合体中的“游牧”文化特质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结构上的联系体现在游牧民的季节性游牧移动上,游牧民根据四季气候的变换,利用起伏高低山地丘陵地形的屏障作用,选择其营地。夏季因气候炎热所以选择山地北侧或海拔较高的丘陵地带的地理位置作为营地,而冬季风大、寒冷所以选择山地南侧或海拔高度较底的盆地等地理位置作为营地。当然这种“游牧”文化特质的构造不仅仅是以合理利用地理环境为目的的,但肯定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游牧民的理性认识系统,融合创造性行为动机形成成为“游牧”文化特质或者说“敖特尔”文化特质的。人类创造的其他文化特质里同样看到地理环境因素作用。例如“战争文化”特质的内容结构中地理环境有关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因素有重要意义。 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台地地处内陆在气候远离海洋,加上海拔高度较高,平均为1000米以上。冬季漫长严寒,大部分地区长达3~4个月,极端最底温度达-40℃。夏季短促大部分地区2个月左右,无霜期段。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大,年较差为35℃左右,日较差为10~15℃左右。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年总降水量为50~450㎜,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种自然条件在生态形成史上易于季节性丛草和落叶丛林植物的生长。蒙古高原的植被深受干旱气候的影响,并且其分布情况与地形结构有关。从植被情况大致分为山地森林地带、草原地带、荒漠草原地带等。各地带植物结构有所不同,森林地带主要有雪松、落叶松以及矮灌丛为主,草原和荒漠草原主要有大针茅、羊草、线叶菊、蒿类半灌木等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蒙古高原种类成分繁多的植物,比较丰富的野生牧草资源。以其为食的动物提供了繁殖生长的客观条件。而这一地带的植物和生物资源保障了人类祖先在这里的生存。人类为了生存对其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社会性活动,就象马凌诺斯基说的那样“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我们的祖先为了满足他的维持生命的需要,有必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进行采集、狩猎和驯养。这种社会性活动标志着草原文化在草原地理环境中的萌芽。 蒙古高原特殊的地理分布、气候及植被状况,决定了这里不利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游牧方式的畜牧业是最适合与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生产方式。草原上的各种饲用植物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人类驯养控制和利用这些食草动物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独特的文化—草原文化。就驯养马为例,蒙古高原上以游牧而生存的人类祖先把食草野生动物之一的马驯养成为家畜,并把它当作游牧生产和交通工具。与此同时古代游牧人就掌握了关于马的知识,陆续创造了有关马的初期文化形态。奠定了所谓“马文化”形成的基础。如马鞍、马鞭、套马杆、马奶酒等物质文化和有关马的诗歌、传说等非物质文化就是人类驯养马直接有关系的。而马的生存繁殖和草原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对该地区生计类型的选择起着很重要的限制作用。蒙古高原属温带草原,其特定的地形、气候及植被分布状况决定了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只能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并且主要以游牧的方式来进行,同时针对这种特定的草原条件及其内部不同的地区差异,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化适应方式”。(3) 以上主要探讨了地理环境对物质文化形成的作用,文化学理论认为物质文化的概念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甚至扩展到人类活动及其物化对象。草原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性质和方式,自然,草原物质文化的形成直接或间接接受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草原地理环境对草原精神文化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有关地理环境对精神文化的影响问题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及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都提倡过。草原地理环境对于非物质文化的形成有一定作用的问题,孟驰北先生在他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影响于人的心理空间,并使其发生各种变化,从而影响非物质文化,以他的观点来说就是隐性文化。“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方面。…草原民族从物质的丰富和各种符号积累的深厚方面虽然远不如农业社会,但丝毫也不能低估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气质。他们的精神和气质包容着人类远古以来就有的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4)“因为他们在旷野、草原、山坳中,各种自然灾害如大雨、大雪、坚冰、山洪、飓风经常光顾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经常面临严峻的挑战”。(5)“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元素,如冒险、进取、奋斗、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6) 总之,草原文化的形成是草原游牧民族适应草原地理环境,改造自然环境活动的结晶。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意义深层结构上的性质无不体现草原地理环境因素的内化。三、草原文化与人文地理环境 人类的发展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人类作为“自然人”存在时,其生命和整个活动都不过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当人类学会进行劳动时,他们不仅把对象世界变成了有意识的存在物,创造出各种各样独特形式存在的文化物质,而且,自己在生产劳动中结成了类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合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劳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文化,人不仅要享受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要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人、社会、文化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地出现的。 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表现为各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关系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社会结构体系。人类的文化创造,促进生产劳动能力,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也必将不断地改变其社会关系。人们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是随着这种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构成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具有独特性质的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上,物质文化的发明,创造,不仅直接发展出了群体、集团、权力、地位等社会本身的参数。而且,这些发明、创造等文化参数作为人的生产劳动能力水平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程度的水准,并且,它们作为物质财富的生产,为社会的存在奠定了经济基础。至于连接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规章、制度等等,它们既是文化系统,同时也是社会参数。 作为一个系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例如,物质文化的发明、创造虽然依赖于社会的需要,但并不是有了社会需要就能创造出科学、技术一类知识文化程度,它很大上依赖于文化自身的积累,这种积累就是文化的独立性。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等文化也是这样,它们并不是随着社会变革立即发生变化的,总是表现出一定的超脱和独立品质。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特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但它的起源、积累和变化是与其一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是社会的历史过程。因为,任何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发展起来的。任何文化都是社会的文化,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社会是人类生产关系及整个互动关系发展的结果。是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社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制度。就是说有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的构成可以说是人类整个生产、交换及互动关系的总合。只有这种关系才能构成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某种特征的社会。 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关系具有这样的特征,文化的抽象化愈多,它的自主性、系统性愈小,也就与社会体系的属性愈小,相反,在抽象化程度不多的原始社会时期,社会与文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进化,社会和文化遂分为不同的体系。但是,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是交互作用的变量关系。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创造,任何文化都不能脱离社会及社会化的人而存在;同样,社会离开了文化就不能进入文明状态。 在人类的生存和延续过程中,社会是整个文化的承担者或载体,是各种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各种文化功能相互整合的单位和代表者。文化作为人类各种集体的财富,离开了社会群体的参与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人类是按照一定的世代积累的文化体系演化的,文化是在各种社会群体的形成、发展及其不断整合的过程中进步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被社会化以利便在特定的社会中生活,享有独特的文化。因此,人类创造的文化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 草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形成离不开草原部落、氏族的游牧社会形态,这也是草原文化的群体属性之所在。人类祖先出现在草原地带并在那里进行社会性活动,同时,草原文化衍生出来,随之不断发展。 人类的形成过程长达数百万年。第一批人类的出现约在300万-150万年之前。考古学界发现在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草原地带约70万年前,早期人类活动的劳动工具及其制造的遗迹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在内蒙古地区发掘的大量古代人类活动场所,如大窑文化等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学者根据对欧亚大陆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研究的成果,提出古人类最早在蒙古高原上形成的观点。进而认为蒙古高原的古人类是旧石器早期的结束阶段由部分采集者狩猎民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及西方等原始人类已经开发的两个区域群迁移到来的。他们在蒙古高原带来了加工石器的技术和用从卵石一侧敲击下来的粗糙石块制造主要工具的传统技术。也有的人类学研究者提出:人类很可能最早出现在位于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草原地带的意见。当然,这些观点各持已见,有待进一步去考证,但从中可以推测,居住在蒙古高原地带的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即已掌握了部分石器的制造和利用,可以用它进行打击、刮削、切割等劳动。 据考古学研究,公元20万至10万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的狩猎民和采集民会用火,也十分熟悉动物的习性及它们的行动时间和路线。他们为了获取大量食用动物知道集体进行围猎,并不断集体迁徒和聚集在公共火堆旁,他们尚未形成禁忌氏族内婚的氏族群。但是,这些群体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有一定的特征,凭体力大小挑选领袖人物,在群落中有一定的宗法性,有一个整套语言信号。旧石器时代的蒙古高原居民已经有了一定的行为规范,这也是他们所面临的组织狩猎,分配猎获物,抵御猛兽和其他狩猎人群的袭击之类的问题,以及开发周围的自然环境的需要而建立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是狩猎和采集可食动物和植物。这种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得不处于游动状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群之间的交往,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在这个时期,草原原始人群中游牧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已初步形成。但游牧业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生产体系的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内陆地区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石器时代比较温和湿润的气候逐渐为干燥和强烈的大陆性气候所代替,从而带来了河床干枯,野生动物逐渐减少,沙丘化过程逐渐出现,形成了中世纪和现代蒙古高原特有的气候,冬天严寒,夏天酷热。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条件,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地带的人们就形成了游牧社会生产体系,基于自然环境条件状态,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在此后一直保持到今天。 游牧业生产体系的形成,大幅度推进着草原游牧人群的社会化,逐渐出现社会分层,并逐步形成草原制度文化。从公元前1000年下半叶开始,在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地带陆续出现各种部落。游牧民族建立国家之前,这些部落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部落为基本单位,以氏族、家庭和亲族关系维系管理和支配民众,编制军队,组织生产劳动,自然形成为一种以“公共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如此的社会组织使草原先民的文化形态步入新阶段,即制度文化阶段。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在蒙古高原地区建立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使草原制度文化推上新阶段的历史舞台,奠定了政治军事体制以及语言、信仰、习俗等文化特质的基础。可以说,草原文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其结构和内涵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结构更多地体现着社会形态,内容方面也显示出更明显的社会等级属性。就匈奴族的社会等级分化而言,匈奴族中已经有了等级制度。据考古研究,匈奴墓葬特点及其墓葬物品说明了匈奴人的等级分层。如阿鲁柴登墓、碾房渠墓等墓出土有金冠饰、金项链、金耳坠等等陪葬金银器,显然是匈奴的部落首领或王的墓。而竖穴土坑墓,一般随葬铜铁兵器、马具和铜铁装饰品等。由此可见早期匈奴族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 匈奴之后,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上先后出现多种游牧部落,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频繁替换统治权,使草原地区的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社会结构松散的状态。就是因为草原文化主要载体的游牧民族社会是一个流动性很强、区域关系复杂,冲突繁多,结构分化和整合频繁的社会,因而其文化特征的形成以及文化综合体的发展受到了相应的影响。草原文化逐渐形成为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相互融合的多元一体文化。 13世纪,蒙古族征服了欧亚大陆,建立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实现了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诸民族的政治统一。统一的蒙古汗国使许多区域性文化开始互相接触交流,而在此前,这些文化在发展中很少把彼此联系,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它文化的存在。蒙古汗国的成立推动草原文化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草原文化在空间上前所未有的传播扩散,影响同时期其它文化,并接受其它文化的异质因素,使草原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总之,从匈奴统一中国北方草原诸民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游牧汗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带诸民族先后被统治于鲜卑、女真、契丹以及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权,形成为传承运载草原文化的“共同体”。同时,他们认同并吸收着农耕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先进因素。国家的建立,使游牧民族社会由氏族制度迈向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游牧民族国家的含义与定居农耕民族的国家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国家的建立,标志着游牧民族的文化由分散不一、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的状态转变为相对稳定而统一的社会状态,并具有了历史传承性的社会形态保障。游牧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对于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游牧民族社会政治结构的民主因素,滋养着草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的发扬壮大。以生命为本、崇尚自然、英雄主义等因素决定了草原文化的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环境共存的生态性特征以及开拓进取、善于冒险的勇敢精神。四、草原文化与游牧经济 文化是人类历程的写照,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经过生存选择而形成的独特生存式样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草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产生和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草原氏族、部落特有的以游牧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和游牧生产方式,这就使草原文化产生了有别于大河流域孕育的农业文化特质和渔猎文化特质。 从宏观角度看,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类赖于生存的主要经济类型之一。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产形式。但是,在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游牧经济何时以及如何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北方以及欧亚大陆草原游牧经济形态形成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形成时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都认为游牧业是由农牧混合经济转化为游牧经济而成的,这个过程通过占据一定的历史时空而实现。这一点已被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所印证。 关于游牧业的形成,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骑马术的出现标志着畜牧经济向半游牧—游牧经济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完成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个转化过程经历较长的时间,大概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间才完成的。在这一期间,中国北方民族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农牧混合经济转为专化游牧经济,也就是畜牧转为游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约公元前1700年至前200年前后,居于北方混合经济中的人群,由于长期的战争习于畜养及利用马匹。而且,在战争迁徒中,他们的一部分也放弃了定居和农业,完全转为依赖马、牛、羊的游牧生业。或者,他们由阿尔泰地区游牧人群中习得这种游牧的观念和技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元前第1000年第1世纪,在欧亚草原各地出现了向游牧业的过渡,形成了新的文化,标志着早期游牧人时期的开始。当然,对整个草原地带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目前还没有根据去肯定经济转型都是同一个模式,不能否定某些人群或部落有直接发展游牧业的可能性。 以摩尔根、泰勒等为代表的西方单线进化论、传播主义学者将游牧经济视为在某个特定地区形成,然后逐渐向其它地区传播。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经济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经济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2、移动的狩猎者从临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从而形成游牧。3、气候干旱趋势导致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群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并季节性地迁移,形成游牧生活方式。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其中的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西方学者逐渐改变了对游牧社会的传统认识,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并非单一,其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农产品。游牧经济并不是“单线进化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形态,而是农业或者其它的经济类型作为辅助手段的混合型经济形态。其根据为游牧民通常并非处在与定居农耕民社会相隔绝的状态,游牧经济也不能满足全部基本需求,定居农业人群与游牧民存在着各种联系。 对于游牧业专业化问题,许多学者将其发生归结于气候条件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认为气候干燥化使得部分牧业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游牧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亦催化游牧业的发生。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和农庄领地的扩展,造成森林被毁,森林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随之遭到破坏,草场资源枯竭,甚至沙漠化,迫使畜牧者迁移逐渐形成游牧。郑君雷先生,对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评述中否定从临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认为欧亚草原及半沙漠地区游牧经济是从食物生产经济转化而来的,并且,这个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历时数千年。公元前3000年时期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从西亚传入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3000年后半叶和公元前2000年)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先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将活动扩散至草原深处。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流动性的牧放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牧放少量大牲畜。公元前2000年代的最干旱气候是定居的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 对于游牧业经济的形成时间问题,可以根据目前的考古学发现,初步断定为“春秋中期偏早阶段,即公元前7世纪前后”。(7)早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尽管有发达的马具,甚至有骑马围猎的图像,表明骑马已很兴盛,畜牧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尚未进入游牧状态。林西大井、赤峰夏家店、蜘蛛山及宁城南山根等遗址均发现房址和窑穴,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铲、石锄、石刀及铜镐、铜鍑等农业生产工具。在遗址内还发现猪、鸡等定居居民饲养的家畜与家禽遗骨。这些发现充分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从事一定的农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鄂尔多斯及临近地区的桃红巴拉文化及杨郎文化,以及燕山地区的北辛堡文化的遗存均为墓葬,很少发现相关的居住址。墓内不再有猪、鸡等,而是以殉马、牛、羊的头和蹄为主,而且,殉牲的数量相当可观。由此可见,马、牛、羊等家畜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财富和生活来源,墓内已无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也正是这个时候,形成了具有浓厚草原气息的动物纹艺术,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游牧业的形成的痕迹。 游牧业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之一,出现在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草原地带,并逐渐形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游牧经济的形成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马克思理论认为:文化是属于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所谓草原型经济的游牧经济是草原氏族、部落世代生存于草原生态环境,为适应环境而选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草原氏族、部落特有的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其文化形态,决定了草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以及基本精神。游牧经济不同于农耕经济,它没有农耕经济那样在空间具有固定性和稳定性。农耕经济主要是以固定的村落与规范的水利设施为基础形成和发展的,农耕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固定性的基础上,为此稳定的安居是农耕经济发展的前提。而游牧经济具有游动性,游牧民族必须经常逐水草而居,处于一种高度的分散游动状态。学术界称之为“行国”,而重土安迁的农耕民族称为“居国”,经济特征决定文化特征。这就是两种文化模式的根本差别。 游牧经济是自然、家畜、人三要素组成的经济形态。它的存在很大的程度上赖于自然界,是因为自然因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占据主要位置,与自然环境的适应,显然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存选择。游牧民族先人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不是采取征服或者是掠夺的方式,而是采取“迁徒—适应”的方式。根据自然条件进行游动式生产,这使其文化形态成为富有动态性格。这种相对脆弱而不稳定的经济形态,决定了草原文化的特征,草原民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缺乏组织化劳动制度的情况下,经常面对大雨、大雪、坚冰、洪水、飓风和蚊虫猛兽等自然灾害及敌对势力,生命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他们却没有难以回避,必须面对现实,为了生存必须迎接挑战,逐步造就出一种不畏不惧、不曲不挠的英雄乐观精神。开放性、包容性的精神文化特质。 草原游牧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虽然对感情的表达淋漓至尽,但塑造悲剧结局情况的很少见,大多数作品都是赞美英雄,以乐观向上的态度战胜眼前的困难作为主要内容的。如两大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就属类似作品。另一方面,流动性的游牧经济不断的扩展、变换草原文化的分布空间,使草原文化成为拥有广阔地理空间的区域文化。并且,游牧经济自身性质所决定的流动性生产、生活方式,赋于草原文化不同于农耕文化,具有开放、容纳,进取,易于接受异质因素的品质,并推动草原文化的结构始终向复合性的方向发展。 游牧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草原精神文化特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对物质文化特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游牧经济形态的形成与游牧民族掌握的生产技术文化的提高,如畜产品的加工、家畜的饲养繁殖方法等。这些技术文化的初步定型和不断完善,带来了以经济技术文化为基础的各种草原文化特质的强化。譬如,奶食品物质文化的产生,为相与奶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以世代生存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习俗为例,其祭祀礼仪中就包含着所谓“白食”的奶食相关的符号象征文化特质。以驯养马为例,蒙古高原上以游牧而生存的人类祖先把食草野生动物之一的马驯养成为家畜,并把它当作游牧生产和交通工具,与此同时,古代游牧人就掌握了有关马的知识,陆续创造了有关马的初期文化形态,奠定了马文化形态的基础,如马鞍、马鞭、套马杆、马奶酒等物质文化和有关马的诗歌、传说等精神文化。由此可见,游牧经济形态的确立,为草原文化主要特征、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草原文化成为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生态型文化。注释:(1)陈建先主编《文化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31页。(2)(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53页。(3)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28页。(4)(5)(6)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32,32,33页。(7)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112页。参考文献:(1)牛森主编《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2)田光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上下)国际文化出版社,1999年。(4)蔡俊生等《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5)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许结主编《中国文化史》花城出版社,2006年。(7)勤尼•格鲁塞《亚西亚游牧民族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8)嘎尔迪著《蒙古文化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9)邢莉著《游牧中国一种北方的生活态度》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百家论坛
草原文化研究、推动草原文化发展
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