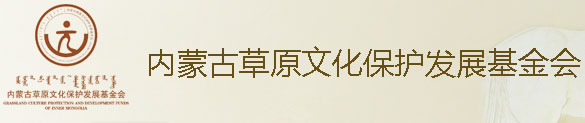
植株特性:高效光合MN209呈半紧凑株型,株高301厘米,穗...
耐密植、抗倒伏、耐瘠薄的玉米品种——MN209。对于广大农户...
MN209玉米种,以其棒子大、穗子均匀、硬粒型品质卓越及高产...
好的种子是丰收的基础,但科学的种植管理同样不可或缺。要想让M...
当前文章:《草原,我永远的母亲--记草原恋合唱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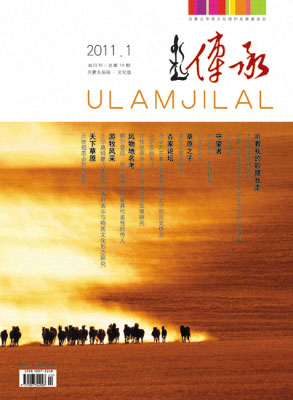
《草原,我永远的母亲--记草原恋合唱团》
在京城,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不是蒙古族,却喜欢演唱蒙古族歌曲,而且用蒙古语演唱;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在六十岁上下,很多人都有在内蒙古草原生活的经历--这就是"草原恋合唱团",他们亲切地把这个合唱团称为"心灵的家园"。
北京城里,业余合唱团很多,约有几千个。喜欢唱歌的人们在合唱团里尽情歌唱,找到朋友,找到快乐,愉悦精神,多彩生活。草原恋合唱团却不止是唱歌,他们的宗旨是"热爱草原、歌唱草原、关注草原、保护草原、和谐草原",并以此为神圣使命。
有人很奇怪,40多年前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被迫中断学业,奔赴内蒙古大草原,或插队或兵团,苦吃了不少,磨难经历了不少,为什么至今他们仍旧念念不忘草原?而他们说:"一受草原养育恩,知青便是内蒙人。"草原,在他们的心里,就是母亲!每一位在草原插过队的合唱团员都能讲出自己心中珍藏的草原母亲的故事。
团长马晓力,1968年7月来到东乌旗道木德公社阿尔山宝力格大队插队。那是个春天,放牧归途,马晓力胯下的黄膘马突然前蹄踏进老鼠洞,跪在了地上。黄膘马站起来就向前跑,已摔下马的马晓力左脚还套在马镫子里,她被黄膘马拖着前行。"幸亏春天穿着大皮袄,我被拖得还不算疼......"但是,马晓力紧张起来,因为就在前几天,北京一名女知青骑马挂蹬,被拖身亡。幸好,"仗义"的黄膘马突然站住了,马晓力得以脱险。她缓缓地走回家,没有向蒙古族大嫂和大姐讲自己挂蹬遇险的事情。然而,几天后,大姐送给了马晓力一双漂亮的蒙古靴。这可是保命靴,因为蒙古靴开口宽松,万一骑马挂蹬,脚很快就能从靴子里脱出来。马晓力知道,这双靴子仅皮子就得花26块钱,几乎是牧民1个月的劳动所得。这双蒙古靴成了她心底永远的温暖。
刘雷音,当年曾在一个春节前,骑马到70里外的旗里买年货。回来时,白毛风刮起来了。刘雷音的脸和耳朵针刺般疼痛,很快没有了知觉。一辆牛车在暴风雪中出现了,一位额吉和一位姑娘冒风雪而行。额吉招手,示意刘雷音下马,然后拉过刘雷音,嘴里念叨着:"霍日黑(可怜)!"额吉轻轻地搓化刘雷音脸上凝结的哈气,又解下自己的头巾,给他把脸裹住。"那条头巾已经不知丢在哪里,但那感人的一幕至今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清晰。"
胡冀燕到井上打水饮羊。天寒地冻,井里结冰了,水打不上来。这时,额吉来了。像是早知道今天要结冰,额吉带来了一个冰锥。冰破开了,胡冀燕给羊群打水,手都快冻僵了。深夜,胡冀燕醒来,发现额吉还没有睡。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额吉似乎在忙着缝什么东西......早上,胡冀燕去放牧,额吉叫住了她,拿出一双白羊皮手套递了过来。"一定是额吉连夜缝制的",胡冀燕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
一天,郑慧莲正在草原上放牧,快收牧了,天气骤变,白毛风刮起来了,一场暴风雪来临。羊群不肯翻山回家,顺着风跑。天黑了,郑慧莲跟着羊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雪原上奔走,不知哪里是家!天快亮了,郑慧莲已经坚持不住了。这时,远处跑来一匹高头大马,额吉的儿子东日布终于找到了她!风雪中,60岁的额吉、十多岁的小妹妹和三四岁的小弟弟,都在拼力轰赶着羊群......郑慧莲心头一热,晕过去了。在她的记忆里,清楚地印着自己躺在额吉家的情景:额吉大手握着自己的手,很温暖;东日布默默地坐在蒙古包边上,看着她;小妹妹跑过来,把热腾腾的面条举到面前;小弟弟站在背后,用稚嫩的小手给她擦眼泪......"如果不是额吉一家人,我肯定冻死了!"郑慧莲泪流满面。
沈和与一名北京女知青相恋,因条件所限,无法结婚。"你们怎么还不结婚?"一天,大队民兵连长问沈和。"没有蒙古包,怎么结婚呢?"沈和说。生产队开会决定,把队里唯一的一顶新蒙古包给沈和结婚用。"你们来给我们当邻居吧!"额吉邀请新婚的两个年轻人。"我们和额吉融在一起了,成了一家人!"沈和说,他和妻子不在家时,额吉就把他们家的活儿全承担了,挤奶、捡牛粪、拉水、做奶豆腐......照顾得无微不至。
如今,这些点点滴滴已经深印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牵挂草原便如牵挂着母亲一般。
"共同的草原情结使知青们经常聚会,大家商量着,成立个合唱团,聚起热爱草原的人们,唱起草原的歌曲。"于是,草原恋合唱团应运而生了。1999年7月9日,马晓力组织曾经在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在京的蒙古族同胞和热爱草原歌曲的人们成立了草原恋合唱团,并出任团长。大家出于对绿色草原和蒙古族音乐的热爱而聚集在一起,在喧闹的城市和市场经济的热潮中,辟一方净土,把那份浓浓的草原乡情融入到发自心底的歌声中。
几十位团员,几乎都没有经历过专业音乐训练,有的连识谱都困难。要唱好蒙古族歌曲,还要用对音准、乐感、声音要求极高的无伴奏混声合唱形式去演唱,难度可想而知。在于杨、咏儒布、娅伦格日乐、阿拉坦其其格等许多艺术家的悉心指导下,在指挥包国庆、声乐指导斯琴高娃等的耐心训练下,团员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演唱得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
草原恋合唱团成立近12年来,演出180多场次,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民族风情,真切质朴的情感,配合以蒙古族歌曲特有的长调、呼麦,诠释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厚重和悠远,深深打动了观众,也感动了团员自己。在北京和国内的合唱比赛中,合唱团多次获奖,受到国内合唱艺术界普遍关注,知名度不断提高。合唱团还以民间文化使者身份前往日本、美国进行文化交流,向世界传播蒙古族音乐及蒙古族服饰之美。2004年7月,在德国布来梅举行的第3届国际奥林匹克合唱节上,草原恋合唱团荣获两项银奖。
随着时间的流逝,草原恋合唱团的团员们大都步入退休的年龄。按常理说,人老了,能经常唱歌,愉悦身心,感受和谐与快乐,安度晚年,这就足够了,但是,他们却不满足于这些,大家的心就像系在了草原上,密切关注着内蒙古大草原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兴衰。当草原兴旺发达时,大家额首相庆,欢欣异常;当草原蒙难时,大家忧心如焚,食寐不香。
2000年12月31日开始,一场长达70多个小时的暴风雪袭击了锡林郭勒盟。在这百年不遇的雪灾中,气温骤降到零下50摄氏度,大批牲畜死亡,冻死25人。
马晓力等人从牧民那里了解了灾情,怎么也坐不住了,萌生了为灾区义演的念头!在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的全力支持下,2001年1月16日,合唱团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举行了内蒙古雪灾赈灾义演,当场募集资金10万多元。1月20日,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再次举行内蒙古雪灾赈灾义演......期间,知青们募捐了近百万的物资。"现场出现的一些场面很感人。好多知青很困难,但是他们有点钱、有点东西都捐了出来......"马晓力说。阎明复会长动员香港慈善组织及个人加入到了这次慈善活动中,一笔笔善款汇成爱的暖流。不久,一批价值1000多万元的物资、药品、食品,被送往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盟灾区。
2007年,草原在连续十年干旱后,又遭遇更严重的旱灾。5月份,正是青草萌生的时节,马晓力、刘雷音陪一位旅居美国的草原知青回阔别30多年的第二故乡。在东乌旗,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干旱的乌珠穆沁草原上牧草稀疏,一片黄色!心中那片碧绿的草原哪里去了?回京后,马晓力夜不能寐,"如果草原不复存在了,我们还唱什么歌呀?"于是,一场"美丽草原保卫战"打响了:7月9日,草原恋合唱团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甘泉基金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行了《留住那片绿色》赈灾义演音乐会,为草原抗旱救灾募集资金......
为了帮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渡过难关,马晓力萌生了给温家宝总理写信的念头,执笔人落在了合唱团文笔不凡的刘雷音身上。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您好!
我们是一群在内蒙古草原生活过的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特别是锡林郭勒盟)连年遭受旱灾之际,我们斗胆写下此信,望您明察、施以恩泽......
曾受草原养育之恩的北京知青
2007年6月24日
6月26日,马晓力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华慈善总会原会长阎明复。阎明复被知青们的精神感动了,他当日把信转往总理办公室。
7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知青们的信上批示:"请良玉同志阅示后转农业部、民政部、发改委、财政部参考。内蒙(古)旱情严重,应予关心和帮助。抄送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温总理回信了!"大家奔走相告。
7月6日,国家派出工作组,奔赴锡林郭勒盟调查旱情。随后,国家相关部委拨付大笔资金,支援锡林郭勒盟等地抗旱救灾......
草原恋合唱团举办的《留住那片绿色》赈灾义演,为锡林郭勒盟募集资金50多万元。这笔资金大部分已经用来为最干旱的东乌旗的苏木打井。2010年8月,他们又用节余的捐款购买了4.5吨优良草籽丸衣扁穗冰草草种,捐赠给锡盟草原镶黄旗,以改善草原植被。
草原恋合唱团一有机会就会回到草原为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演出,东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呼伦贝尔、乌兰浩特、恩和贝......,还连续两年参加锡盟的春节晚会、在锡盟电视台录制节目。他们牵挂着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曾经多次捐资救助草原的孩子。无论是在北京治好了髋关节脱位的毛毛,还是安装了人工耳蜗终于能听到声音的欧索亚拉,她们和她们的家人都很感谢草原恋合唱团的团员们,以及帮助过他们的所有老知青。
"草原额吉没有白疼你们!"马晓力和她的团员们捧着这块东乌珠穆沁旗父老乡亲赠送的牌匾,像是孩子得到了父母的表扬,幸福地微笑着......
草原,在他们心里;母亲,在他们心里!
(注:文中蓝色部分为选摘《北方新报》记者张泊寒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