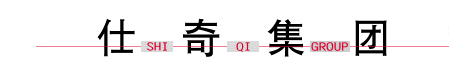●杨·道尔吉
显赫的湖滩河朔
对于“湖滩河朔”这个地名名词,我一直感到很费解。“湖滩河朔”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名词在发音上是否含有满语或者蒙古语的因素?到现在我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关于“湖滩河朔”的所在,我是知道的。黑河从土默特平原倾泻而南下,注入黄河。入河之处,曾经有一个大湖滩,靠西有一个冲积的平川,就是“湖滩河朔”。“湖滩河朔”就在明代的那座托克托的城下。
今天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呼和浩特市南部靠近黄河处就是托克托县,县城西南有一个平川,夹在黑河与黄河两条银带之间,这里的许多地名今天仍然保留着。
“滩”的痕迹,诸如“中滩”、“柳林滩”、“下沙拉湖滩”等等,黄河对岸有“巨河滩”,顺黄河而下30里则有“蒲滩拐”的地名,都与“滩”有关联。可是这些纪念性的地名仍然让我们无法理解那么显赫的“湖滩河朔”地名怎么会消失呢?
公元1696年阴历十月尽,黄河流凌。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巡省边隅,来到黄河岸边,赋诗一首,题曰《黄河》。在这首诗前有一篇《序》,共254字,提示自己“临河增思,诗示永久”。序文开首则写道:“河源发于塞外,流经万里余,始由中土入海。曩曾遣使探流穷源,河之为利为害,莫不洞悉。近以巡省边隅,驻跸湖滩河朔……”
《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十月:“辛亥,上驻跸湖滩河溯”。
康熙的《诗序》里记写为“朔”,《清实录》则为“溯”,我们保留了原貌。不管取用哪个字,康熙皇帝的行宫曾经在“湖滩河朔”这个地方驻跸过。
调军远征
康熙来到土默特地方的黄河岸边,是在部署一场接近胜利的战争,并且在等待这场战争的胜利结束。这场战争是康熙皇帝刚刚完成了平定南方三藩之后,与蒙古准噶尔部领主噶尔丹之间进行的。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纠葛,前前后后已经进行了6年之久。1690年发生在克什克腾草原南部乌兰布通之战,拉开了清朝与准噶尔部的战争序幕。乌兰布通是清朝地界,且距北京仅700里。噶尔丹侵入,清朝不得不遣派重兵出击。1690年七月初二,康熙皇帝命皇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各组成一路大军北出喜峰口迎敌。此外,另有和硕简亲王雅布,皇长子胤禔,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均参赞军务。七月初六,两路大军10万人马先后出发。七月十六日康熙皇帝也曾启程北上,但中途因病返回。乌兰布通战役是在1690年八月初一开始的,噶尔丹只有2万余人,虽然顽强,但终于抵不住清军的火炮攻击。清军火炮营统领、皇帝的舅舅佟国纲战死。和硕裕亲王福全等建议暂缓攻击,给噶尔丹以喘息的机会,噶尔丹夜渡西拉木伦河逃走。
1692年,噶尔丹无端擒获并杀害了清朝廷派往准噶尔部的使者,激怒了康熙帝,促使康熙皇帝下决心剿灭噶尔丹。经过长达4年的休整,双方都加紧训练军队,准备充足的马匹和粮食,积极备战。
1695年夏天,康熙皇帝便命侍卫内大臣、伯爵费扬古率军在归化城待命。费扬古早在两年前就已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归化城。11月,康熙皇帝征求诸大臣的意见。大多数人都以为立即出兵为时尚早,只有费扬古提出宜马上出击。康熙皇帝力排众议,采纳了费扬古的上疏,决定兵分三路,向西北挺进。费扬古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负责西路军行动;东路军由萨布素将军指挥,集结于克鲁伦河下游,以防噶尔丹东窜。康熙皇帝亲自率领中路军共计10万人马,由北京出发直接压向克鲁伦河中游。这10万人马中只有3万多兵士,剩下的都是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1696年2月30日,北征大军出发。在这支浩浩荡荡的军队中,有一位随军小贩,叫王相卿,日后成为著名的“走西口”人物,因为他是旅蒙商号大盛魁的主要创始人。
两个月后,康熙大军逼近噶尔丹的营地,大清皇帝的敕书送到了噶尔丹面前。噶尔丹登高一望,确信康熙皇帝亲自前来,便下令向西转移,沿途一片混乱。5月13日,噶尔丹的先头部队与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相遇于漠北昭莫多地方,拉开了昭莫多战役的序幕。结果噶尔丹又一次溃逃。
1696年六月初,康熙班师回到京师。西路军在费扬古将军的率领下也回到了归化城。但是康熙皇帝在京城只住了100天,便于同年9月19日来到了归化城,10月来到了湖滩河朔,继续指挥彻底剿灭噶尔丹的战事。
湖滩河朔是屯粮之所
康熙皇帝的行营驻跸在开阔的湖滩河朔,旌旗招展。已经被招抚的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竞相前来朝觐。康熙皇帝除了“临河增思,诗示永久”以外,还要做其他的事情。1696年阴历十月二十三,皇帝发出一道命令,“命督运于成龙等,运湖滩河朔仓米一千五百石至大将军费扬古军前喀喇穆冷(黑河)地方”。(《清圣祖实录》)。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件事情的可信,康熙皇帝还留下了一首诗:“土墉四面筑何坚,地压长河尚屹然。国计思清荒服外,早将粮粟实穷边。”
清初的国策曾有“封禁边门”的相关律条。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曾经颁布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的禁令(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166)。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再次下令封禁边门,设官卡稽查,杜绝流民出口。但是,乌兰布通战役之后,塞外的土默特平原成了“总要之地”,成了清廷用兵大西北和漠北的出发地和后勤保障基地。凡事都要变通,在这种原则下,招募“走西口”的寄民开耕土地也就情有可原了。
1692年,兵部奏请在归化城设将军一员。1693年5月,费扬古为安北将军,率军驻到归化城及其附近,需要粮草供应。
1692年,从京师通往蒙古各旗的驿路开通,西口外设立了许多驿站。
1692年至1693年,康熙皇帝连续两年派官员在归化城地方督耕,将所收莜麦、糜黍、大麦贮于归化城仓。
1694年,为解决驻军粮饷远途押运的困难,清廷又从边内招募民人出塞耕种垦殖。
1695年,清廷在两翼黑河、浑津等地设十三圈庄头地,垦地共二百余顷。
大量的军队移驻和招民垦殖,使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再一次发生变化。16世纪的板升移民,主导者是蒙古土默特的封建领主。而此次“移民入军”,主导者则是清朝中央。大军压境之下,蒙汉百姓只能顺从。
那么“板升”呢?既有“板升”,为什么还需要招民垦种呢?原来,板升在清初已经遭到清军的破坏。17世纪30年代初,清(后金)军队在皇太极的“烧绝板升”的使令下,只留寺庙,不留村庄。让土默特地区的板升农业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如果再兴农业,就需要招民垦种。
康熙皇帝的游兴
康熙皇帝在湖滩河朔等待着前方胜利的消息,还要游览黄河两岸。1696年11月6日,这一天天气晴好,康熙皇帝在黄河的转弯处的军渡口命令军士分三路在结冰处垫土,然后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境,在今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北部围猎,捕获了很多雉兔。赐见了前来拜谒的鄂尔多斯王公,赞扬了鄂尔多斯的民风和物产:“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其他蒙古殷富。围猎娴熟,雉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
1697年早春,康熙皇帝从湖滩河朔进入鄂尔多斯,穿过准格尔旗而到达长城,然后沿长城西行,西渡黄河进入宁夏。3月,得到了噶尔丹病死的消息,遂从宁夏横城堡漂流而下。4月15日,到达湖滩河朔登岸,谕令在湖滩河朔再建粮仓50间(原有150间)。
康熙皇帝对西口外的游览影响深远。1697年,朝廷准许口内汉族农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垦殖。“春至秋归,谓之雁行”,没有形成定居地。同时,允许开垦鄂尔多斯与晋陕交接地区的“禁留地五十里”部分地段。黑界地有些地方成了白界地。